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渐渐低垂,最终被呼啸的风声取代。从高空俯瞰,整座岛屿的轮廓在薄雾与晨光中逐渐清晰——锈色屋顶的仓库群像火柴盒般堆叠,倾斜的钟楼在废弃城镇边缘投下长长的影子,麦田的金色波浪间藏着生锈的收割机。这就是我们的战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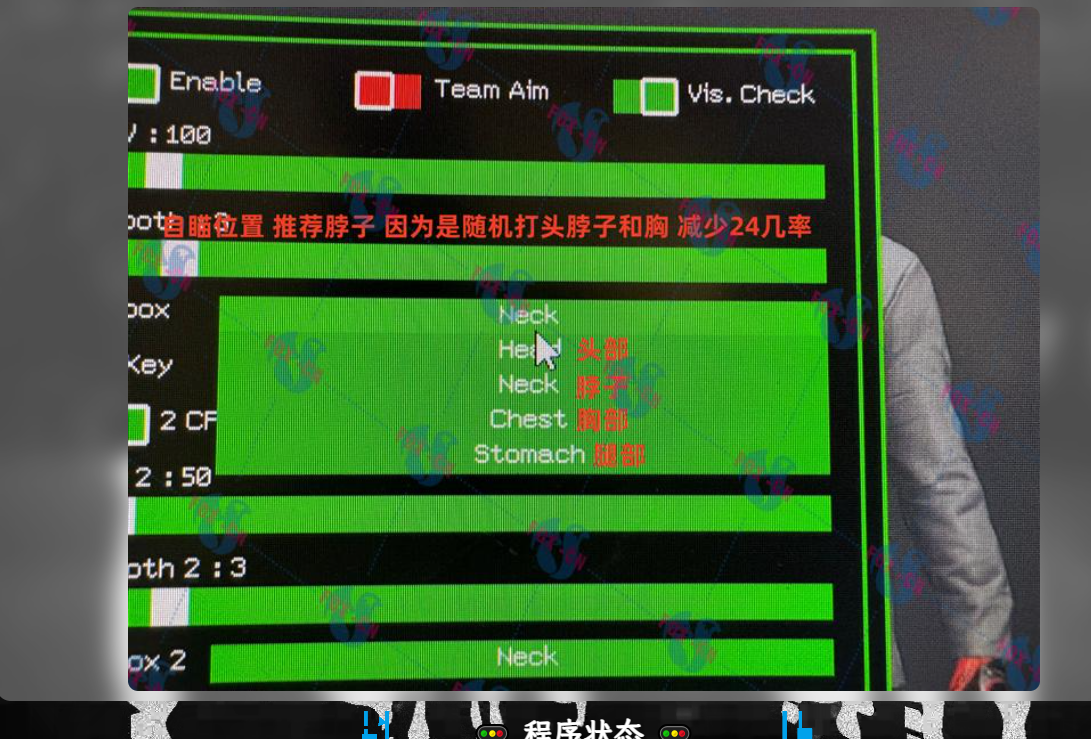
风在耳边尖锐地嘶鸣。我调整姿势,向着那片墨绿色的山林俯冲。降落伞“嘭”地张开时,整个世界忽然安静下来,只剩下帆布摩擦空气的沙沙声。下方,被遗弃的防空洞入口像大地的一道伤疤,半掩在蔓生的野草中。更远处,湛蓝的海水反复舔舐着码头腐朽的木桩,每一次潮汐都带走些许时间的碎屑。
枪声总是突然炸响。有时来自山坡上那栋孤零零的红砖房,有时从水城迷宫般的巷道里反射出回音。我蹲在二楼破碎的窗后,看着弹道像发光的针,短暂地缝合着废墟与废墟之间的空隙。地图上那些没有名字的角落往往藏着最真实的生存法则:歪倒在田埂的拖拉机可以提供完美的射击角度,学校体育馆看台的阴影能吞噬整个小队的脚步声,就连P城教堂塔尖那只永不鸣响的铜钟,也曾为多少狙击手标注过风的轨迹。
毒圈开始收缩了。淡蓝色的屏障温柔而致命地掠过原野,所经之处,荒草低伏,鸟雀惊飞。必须穿过那片开阔地——地图上短短两厘米的距离,在这里是五百米毫无遮蔽的死亡地带。我数着心跳奔跑,子弹掀起身旁的泥土,温热、潮湿,带着根茎断裂的气息。当终于滚进反斜面的草丛时,背上的三级包侧边已留下一道焦黑的擦痕。
决赛圈缩在了石阵废墟。七根巨大的玄武岩柱在暮色中矗立,像远古巨兽的肋骨。我趴在最粗的那根石柱后,听见四面八方传来细碎的声响:金属轻轻刮过石面的摩擦声,能量饮料拉环被小心撬开的脆响,还有压抑到极致的呼吸。地图在此刻失去了意义,比例尺放大到每一块碎石的棱角,等高线具体为膝盖下土壤的坡度。当最后一声枪响在石阵间回荡湮灭,胜利的字样浮现在视网膜上时,我突然听见了海浪的声音——原来这片杀戮之地,一直温柔地被潮水包围着,只是我们从未真正倾听。
夜幕终于完整地降临。那些交错的弹痕、散落的弹壳、尚未消散的硝烟,都将被月光浸透,被晨露稀释,等待下一次飞机引擎划破黎明的寂静。而地图上那些沉默的坐标,将继续见证无数个这样开始与结束的轮回。